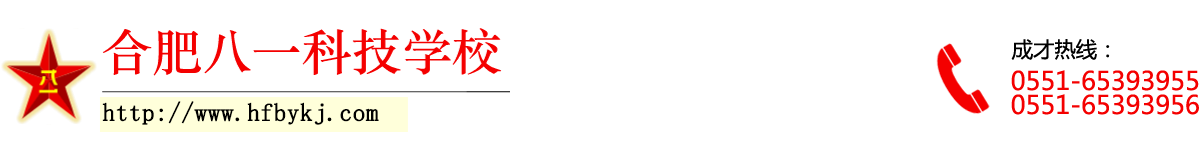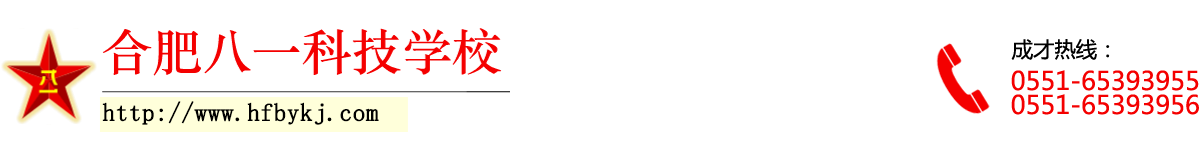|
我定期去弗吉尼亚北部阿巴拉契亚山麓的一个教堂墓地,拜谒我的祖先,这一次次拜访可以减弱世俗浮华的诱惑力。
先辈们就长眠于庄严的砖砌教堂后面,教堂有一个高高的方形砖砌的钟楼,非常普通,并不华丽漂亮。在此安眠的先辈中有些人曾参加过这座教堂的修缮工作,另一些真正的老祖宗们甚至就曾参加建造此教堂,但我不能断言,因为毕竟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。
墓地景色那么迷人,特别是初夏,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,真是遗憾。野玫瑰在碎石围栏上怒放,春白菊开满大地。和煦的微风缭绕山头,如黛的群山伸向西方。
墓碑并没有什么可观赏的,我一直就这样认为。但它们的确帮助我们追寻家族的印迹,它们还有一个优点,就是从来不象家里人那样对你唠唠叨叨。
这并非说墓碑不说话,不能和你交流。每次我经过刘易斯叔叔墓碑时,总会听见他说:“孩子,回头到理发店来,我给你把头发理理。”他是一个理发师,有一段时间他离开故土去巴尔的摩城里,但最终还是回来了。那些曾经出去的,最终几乎都回来了,而大多数人却一直都呆在这里。
当然了,这里并不是教堂墓地,而是在离这里三、四英里远的田野里。祖母于南北战争结束那一年,出生在森林边上延绵起伏的土地上。在离森林大约三英里的山脚下,她度过了大半生,如今已在这棵古老的绿荫树下安眠了解50年。
长辈都不是那种远行的人,亨利二伯,一个木匠,就葬在祖母身边,他就在家乡度过了87年,对没有去过巴 没有丝豪抱怨。如果想让亨利二伯说话,除非你去问路。
“到学校怎么走?”我问到,当然声音不大。
“顺那条路走,好长一段路哩。”他答到,仍是我孩提时就记得的那个含糊不明确的指路人。象这样访刘易斯叔叔、祖母和亨利二伯很有益。他们不为北约组织的现状而担忧,也不为美元疲软而嘀咕,与他们交流能提高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。
长者总是看得开,想得远。当然你不可能用那么深远的目光看待一切,但是适当地采用是有好处的,这能调整血压,避免冲动,从更明智的角度处理好问题。
适当地看开一点,你就会明白,在地铁里被人中踹了一脚并不是 严受到伤害,无需怒 冲冲。
我曾祖父安眠在附近的某个地方,他生前就住在山脚下,以造猎枪为生。但我从没有见到过他的墓,他生于是1817年(詹姆斯-门罗总统时代),我真想找到他,与这样一个生活在安德鲁-杰克逊(美国第七任总统,第二次反英战争时的将军)鼎盛时期的亲人交谈交谈。
我那位曾祖父经历过杰克逊总统、亚伯拉罕-林肯总统及南北战争时代,对如今发生的事情不会有什么印象,而我却想从他的墓碑上得到点反响,那怕只是对我这个没有经历过真正危难岁月的重孙的冷淡轻蔑,也会使我欣喜颤抖。
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他,但找到了伊维大伯。他是一个公然的胡佛派共和党人。我对他的墓碑点头招呼时,听到他说:“孩子,把那些刀豆都吃了吧。”
令人惊奇的是埃德加叔叔,他已长眠在此好几年了,但以前一直没有见他的墓。因为他是们重要人物,棒球队的经理,所以我不敢打扰他。我叔叔哈罗德和我堂姐夫霍华德是他队里的两个投手,他们被对方在投球区连连得分,埃德加叔叔只得问游击手,能不能临时充当投手去投球。
虽然我没有找到制造猎的曾祖父,但在离开的路上见到另一位曾祖的墓碑,这们曾祖与众不同的是他只留下了3.87美元的遗产。知道这件事以来,我是******次从这条路经过,我不由地笑了,但一个声音在说:“孩子,最终我们和大富翁洛克菲勒的财富是一样多的。”于是我钻进汽车,穿过开满春白菊的田野,经过充满玫瑰花香的石栅栏,驶上大道,对这个世界加心满意足了。
(此译文获第九届“韩素音青年翻译奖”******奖) |